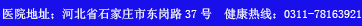日本平安朝器物对女性美的烘托
2022/10/2 来源:不详白癜风的治疗方法 http://m.39.net/baidianfeng/a_4249431.html
《源氏物语》是一部日本古典文学的标志之作,在日本的地位与《红楼梦》在中国的地位相同,它被誉为日本物语文学的高峰之作,对日本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并持续的产生着巨大的影响。
作者紫式部在《源氏物语》的《梅枝》卷写道:“嵯峨帝所书《古万叶集》选集四卷。延喜帝所书《古今和歌集》,纸为唐国浅缥色纸所继,封面裱以绮罗,为同色较浓纹样;同色玉轴,书绳为缎制,作唐式式样,优雅无限……”
可见当时器物打造何其讲究,仅仅是一本拿在手里看的书,就如此独具匠心,它呈现的是一种优雅的美感和极致的韵味。器物只是器物,但有了人,就赋予了它万千灵动与美感。
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,古代从中国学习,近代从西方学习,使他们在没有自己文化的同时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文化,不过他们更精于细节,把学来的一点皮毛发挥到了登峰造极。
中国古典器物除了实用性,更是对天地万物、自然界的观照而打造的艺术品,人们把居室器物、种种日常用品与自己的生活习俗相互融合,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状态。女性养在深闺,日夜与这些器物相伴,就衍生出了一种另类审美,这种审美就是人与物相互烘托,映衬出一种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含而不露的独特美感,这种美是物与人浑然忘我。
照搬了唐制一切的日本平安朝,又有哪些这方面的独具匠心的改良与传袭呢?这些我们在《源氏物语》及平安朝其它女性文学可窥一斑。为了便于我们阅读和理解,日本文献学学者池田龟鉴把这些研究结果收录在《平安朝的生活与文学》一书中,我们现在就去了解一下吧。
一、半遮半掩的隔物制造的幽雅之美
日本平安朝自公元年到公元年,对应的是中国晚唐、五代十国、北宋前期的时代。盛唐时期日本派来大量僧侣来学习大唐文化、经济等各方面的成就,大唐也相当大度,并赠送许多经书给前来学习的日本学者。这样的结果就是,日本几乎照搬了整个唐朝的体制,包括都城的建造也完全按照唐都长安城而设计。因此自从日本迁都平安京,沿袭的就是中国传统的那一套,关于器物与美学的关系也与中国毫无二致。
在古代,中国女性不能显露于前朝,只能活动于后宫,但在实际的操作中总也少不了她们的参与,于是这些身影总在半隐半现中显现。这半隐半现就是在器物的帮助下实现的,然而经过历史的不断的发展与沉淀,这一习俗就造就了古代女性一种含而不露、隐而不现的独特审美观念。
“一帘幽梦”、“犹抱琵琶半掩面”就是这种审美在文学作品里的充分体现,而日本更是把这一审美情趣也照搬了去,并用他们独制的器物来将这一切更完美的表达。
1、竹帘
竹帘是设在母屋及厢的周围,呈方形,用竹编制而成。竹帘上方的绢比较宽,称为“帽额”,边缘包有萌黄色的绢带,绢上染黑色窠纹。
2、壁代
壁代里侧为白色,打磨出光泽,有七幅绢宽,紧贴着帘的内侧悬挂,在表侧还绘有朽木形或花鸟纹样。壁代的每一幅绢都各分表里,而且每一幅绢都有一条宽三寸的绢带。壁代与竹帘形成一种色彩对比,在豪华绚丽之中呈现出沉稳的宁静感。
3、几帐
几帐的形制,是在称为“土居”的方形木台上坚直固定两根称为“足”的圆柱,上横一根称为“手”的横木,帷子就挂在这根横木上。几帐的高度有三尺和四尺,手长必须是足长的倍数。如果是四尺高的几帐,帷子就要长六尺,分为五幅,每一幅中央都有称为“野筋”的两条长带。
野筋最初是表为红色,里为浓红色。后来表不变,里改为了黑色。几帐的手和足涂黑,夏季的帷子会在生绢(直接用生丝织成的绢)上用胡粉绘出花鸟,冬季则在练绢(用生丝脱胶后的熟丝织成的绢)上绘制朽木形的图案。
4、扇子
扇子是女性日常生活的重要用品,在宫廷之中它的功用就不是扇风改凉这么简单了,更是一件女性随身的装饰用品。所以对扇面、扇柄、坠穗的设计与讲究都煞费苦心。
竹帘、壁代、几帐、扇子这些器物的作用并不仅仅在它们的实用性上,而是与女性的结合,更造就一种半藏半露的“幽雅”美感。竹帘、壁代、几帐表面是为区隔房间,但女性利用这些室礼,半遮半掩,只露出身体的部分,有时甚至只露衣服一角,这些恰如其分的表现手法使女性的美显得更深厚、更优雅。
室礼是静止的隔物,而扇子跟随主人,半遮半掩中则更显灵动。《紫式部日记》中写道:“将扇半掩之侧颜,华美清丽”、“(众女官)皆以扇掩面,仅得略窥额头。纵便如此,仍可明其容貌高下,此亦奇也”,表现的就是扇子奇妙的功效。其实扇子不管怎么用,都要露出眼睛,它展示的就是一个人最集中的核心,一颦一笑更见心思。面容虽或遮或掩,却能更直达观者的心灵。
在《红楼梦》中落魄书生贾雨村,正是在与甄仕隐婢女娇杏不经意间的一秒眼神交汇中定下了终身。没有任何言语,没有任何告别,多年后中举归来的贾雨村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来甄府迎娶娇杏,是什么让贾雨村笃信了娇杏会等他一生?我们不得而知,唯一知道的只是,人只需一眼就能在对方里看穿他(她)的一生。深幽曲径的心思,就藏在这半露半掩之间。
二、朦朦胧胧的灯火制造的神秘之美
在现在,日夜灯光通明,人们已经很少享受到月光、火光的照耀,很少能体会在那种幽静冷清的夜一片皎洁的月光、一盏摇曳的灯火制造出的美感和淡淡心事。人似乎离自己越来越远了,很少有一刻这样与自己相处。我甚至怀疑,现在人们家庭不睦、离婚率提高、亲子关系恶劣都与这一点有关。
很多年前,曾经看过一篇文章,写妻在冷清的秋夜里,在灯火摇曳之下织毛衣的景象,那位丈夫处在数着时光静静流淌的光景之中,居然满心涌起的是温柔的情思,生怕打破了那一刻的美好。
影影绰绰灯火下的妻,是美的,是好的,是抹去了日常一切纷争的温柔的妻,满足了一个丈夫对女性所有美好的想象,那在平安朝的宫廷里都有哪些点亮灯火的用具,更能烘托出了女性之美呢?
1、灯台
在平安朝,灯台分为“结灯台”和“切灯台”,基本形制是在长杆顶端设一托盘,盘上有水平的金属杯,杯上载以“油坏”,然后往油坏里注油、放灯芯、点火。
2、灯笼
灯笼为木制,横截面呈四边形或六边形,笼顶屋檐涂黑,檐端内倾。各面的窗户贴以薄物,顶部有挂钩,以布条悬挂。
3、脂烛
脂烛为松木所制,长一尺五寸,直径约三分,削作圆柱形,顶端用炭火烤焦,涂油后晾干,柄的部分缠以薄墨色的纸,这是在室内使用的,在室外使用的则是松明。除此之外,还有一种室内室外皆可使用的脂烛,叫立明。
4、篝火
篝火是在铁笼中放入打松(就是松木段),点燃后作用照明。
在《源氏物语》中就有多次描写灯火对女性之美的观照,如《常夏》卷中:“(玉鬘)因此和琴之事,近至源氏之侧。(问曰:)‘不知何种风来,方有如此琴音?’将头微偏,侧耳倾听。灯火之光照映面容,美不胜收”,又如《篝火》卷中写道:“(于篝笼中)入打松稍许,略微退后,燃起篝火。(玉鬘)屋中清凉依旧,照明恰到好处,更显佳人美色非凡”等等。
灯火确实给人一种别样的美感,朦朦胧胧、影影绰绰之间,一团光亮的火星不停地跃动,把一个静下来的夜制造出生命的动感。女性在这样的光照下,才显现出了与白日隐藏完全不同的光景,她们放松规矩之下的拘谨,做一刻真正的自己。她们可以豪放可以矫情,甚至可以泼辣可以轻佻半刻,完全释放自己。
灯火是一个家庭里家常的温暖,更是一个女人璀璨的美丽,世界在这一刻为她们改了芳华,她们每一个都成为了十八岁,可以毫无顾忌地释放她们的美丽。世界需要这一切,她们抚慰了生灵,籍慰了人心,使人们在这一刻洗尽了铅尘,在次日能以一颗更洁净的心融入红尘。
三、华美别致的车舆制造的飘逸之美
马蹄声儿嘚嘚响,那是属于男子的豪放,而在深宫里的平安朝女子,则只能乘坐在牛车里缓缓向前。
可是各位看官,千万别误会,日本所说的牛车并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牛车,我们的牛车是用来拉货的,它不载人。而日平安朝所说的牛车,是几乎除了辇之外的所有车。辇分为凤辇和葱花辇,只有天皇才有资格乘坐,而皇后和斋王只有有特别的敕许,才可以乘坐辇,就是说在日本除了天皇,所有人乘的几乎都是牛车。
牛车分为唐车、槟榔毛车、槟榔庇车、丝毛车、半蔀车、八叶车、网代车、网代庇车、雨眉车等。而宫中女房可乘的牛车,大体限定为槟榔毛车、丝毛车、半蔀车、八叶车等。
1、槟榔毛车
槟榔毛车是将槟榔叶撕成毛状,葺在车厢顶部及侧面的车辆。只上皇、亲王以下,四位以上的公卿、高僧、女房等有资格乘坐。据《枕草子》记载,当中宫行启到大进生昌的宅邸时,女房清少纳言就是乘槟榔毛车同行的。
2、丝毛车
丝毛车是在槟榔毛车的基础上将丝毛染色,葺在车顶部及侧面的车辆。根据染色不同,又分为青丝毛、紫丝毛和赤丝毛等。青丝毛,是皇后、中宫、东宫、准后、亲王、摄政等才有资格坐的,是规格相当高的。紫丝毛是代理女御、更衣、尚待、典待等坐的,相当于说只有拥有中高级职称的人才有份。
而赤丝毛专供参加贺茂祭的女性敕使乘坐,贺茂祭的女性特指天皇依例送至京都贺茂神社侍神的未婚皇女,也称斋王。
3、半蔀车
半蔀车的车顶是用桧皮斜编成网状,青地黄纹,在侧面有半蔀,以供乘者向外观看。上皇、摄政、关白、大臣以上的官员有资格乘坐,高僧和上臈的女方也可以乘坐。
4、八叶车
八叶车的网代为萌黄色,上缀黄色八叶纹,故称八叶车。八叶车又分为大八叶和小八叶,女房基本上只能乘坐小八叶。
坐在车内,外人不得见,何以显示其美呢?日本人可是别出心裁,想出了“出车”一法。那何谓“出车”呢?
出车就是女房在乘车时“出衣”。怎么个出法?就是女房将自己的衣物从车的窗帘或下帘下露出。下帘是垂在帘后的一层帐幕。
日本还为出车立下了规矩:女房要在车内露出袖口和褄(长衣下摆左右两端部分),女童则要露出袴和汗衫下摆。《源氏物语》中就写到了出车时的情景:“乘车观赏之事,(路上众人)期待已久。一条大路水泄不通,嘈杂喧阗。各栈敷之装饰皆弹精竭虑,女子袖口亦令人大饱眼福”、“有如前述,各车精心装饰,更胜平日。(车中女子)争相于下帘下出衣,斗艳争辉……”、“下帘纹样等处,极具雅趣。(乘车人)坐于车厢深处,仅将袖口、裳裙、汗衫等略微露出,衣物色彩精美……”,这样的描写真是让人大饱眼福,如身临其境般见识到了当时的华美盛况。
女房们被牛车载着缓缓前行,色彩纷繁的袖口和褄从车窗的帘或下帘中露出,微风拂过,形成细微的滚滚波浪,可见各种高级丝物轻盈飘逸,显示出一种无比浪漫的风雅,真是美不胜收。外物与人相互烘托,相得益彰,呈现的是器物与人合而为一的动人美感。
与现代女性美强调个人气场不同,古代社会男尊女卑,故意去女性个性化,然而女性的美却毫不比现在减弱一分。那时的女性美失去了彰显个性的机会,但她们的美却像空气、像流水一样无孔不入,使器物站染了她们的灵性,反过来映衬她们的美,不但对她们的美没有丝毫减损,反而使她们的美更增添了一份奇异的韵致。
在平安朝里生活的女人们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,一千多年后的人们会从残缺的古籍里,会在吉光片羽的残片中,寻找点点滴滴关于她们的美的记忆。因为现在科技无比发达,人们几乎要什么就有什么,然而却偏偏少了那份美的韵致,少了人与器物之间相互依赖相互流转的美的律动。
生活在古代的女性是悲苦的,但也是幸运的,就如今日的我们,挣脱了压制我们的樊笼,但也多了一份我们难以扛起的责任。生活于我们是一样的,但我们留给生活的,可以是一份永远无法消散的别致的美。